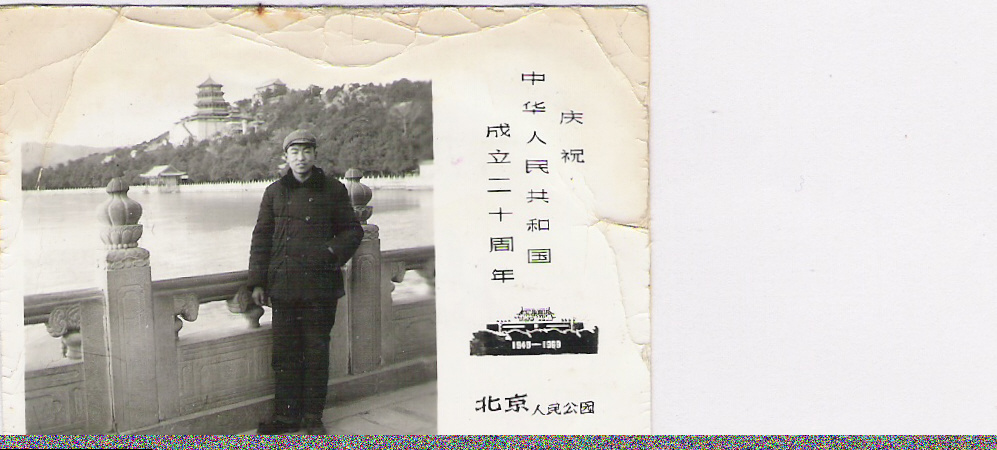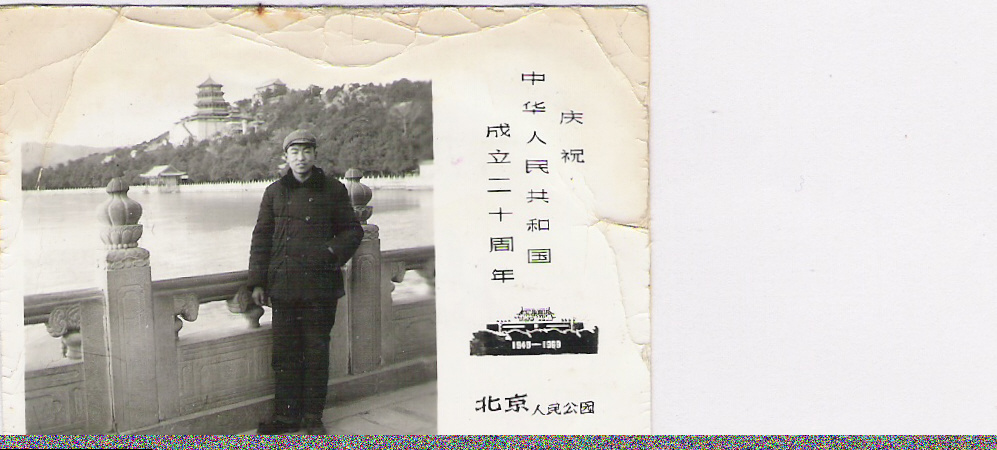| 不再产生“田园诗”的时代
——读“田园诗”有感
(二)
……
恍惚间,我突然想到——为何自清代中叶以降,就不再或者说很少产生真正的山林田园诗了呢?为什么现在不会产生田园诗人和田园诗呢?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林田园大多依旧,但田园诗人和山林田园诗却突然销声匿迹了。
如若要追究这个问题的历史、社会、经济原因,那就说来话长也不是在下力所能及的。这里只就现在为何没有了写出山水田园诗如陶(潜)大小谢(谢灵运谢脁),孟(浩然)王(维)韦(应物)范(成大)等那样的诗人而说说自己的看法。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隐逸之风的盛行,为山水诗派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从六朝陶渊明、谢灵运,到盛唐时期的孟浩然、王维直至储光羲、祖泳、常建、裴迪等。他们隐逸的原因和方式不尽相同:或是入仕前养望待时,或是失意后不满现实,或是厌倦政治,潜心佛老;有的隐居山林田园,有的是亦官亦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曾经长期或较长时间居住乡里,他们都热爱自然,讴歌山水田园,并互相酬唱,形成流派。而反观如今,类似的(诗)人却都消失了。
首先以写下了大量田园诗的陶渊明来说,他三十岁左右进入仕途,或出或入,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去职,归隐田园,息交绝游,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活。他有着一般文人所未曾有过的田园农耕生活经历,和劳动人民有许多接触,可以说,是生活给他以厚爱,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而现如今有类似资历的士(诗)人如作家们都忙着干立竿见影的活去了。给名人作传、替企业家捉笔,最不济的也在报刊上开个专栏,悠哉悠哉,谁还去写诗啊?更别说让耐不住寂寞的他们到山乡长住,去体验,去写田园诗了。
再以天宝初曾在终南山和蓝田辋川过着亦官亦隐生活的王维和晚年隐居家乡石湖的范成大为例。现在的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高中级干部)在位置上赖至70岁,起码要在政协挂个名,直到走不动了,谁还会回乡下去呢?且不说那些省部级以上高官,离(退)休后都无一例外地住进了戒备森严的别墅、大院里;就是那些中小城市的官员,一屁股住进“市委大院”、“干部小楼”就再也不动窝了。这官位虽不能象我们友好邻邦的领袖家那样代代相传,而象征着权力和权利的干部房,接班人却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况且一离开当初掌权所及的势力范围,起码你生病叫车去医院都得自己掏钱打的,更别说搬到穷乡僻壤去住了。再说你当初费劲提拔上来的接班人,人一走,茶就凉。你走远了,就更借不上力了,那不是当初白费劲了吗?另外,现时的这些人,当权在位时,就不好这一口,还能指望他们写田园诗?
还有本就住在农村的人,身强力壮的或者能出去的,都直奔东南打工讨生活去了。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小的拉不开弓,老的舞不动棍。老的30年前扫盲班(这30年来还真很少听说办扫盲班之类的事)学的几个字都已忘光了;小的归入了“留守”儿童的行列,想靠这些人写东西,那更是不着调了。
即使有个把坚守家乡的知识青年,辛辛苦苦写出几首有关家乡、山林、田园的诗,又到何处去发表,又怎能传之于世呢?
因此,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不会再产生新的田园诗的时代了!
只能是一声长叹!唉…
好在我们还有《陶渊明集》在,有《谢康乐集》在,有《孟浩然集》在,有《王右丞集》在……它们至少能让身处都市喧嚣中的我们,体会片刻忘我的田园闲适和惬意吧。
二0一0年十月十三日
|